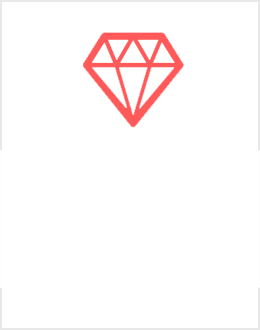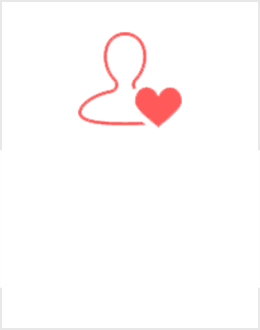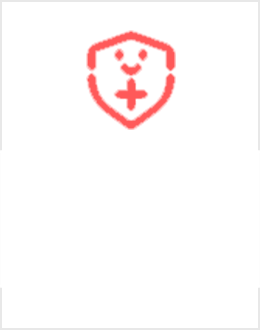俗话说,有啥都别有病。真真的,有病太痛苦了,若只是简单的小病还好,吃上几付药,便能好了;若是生了治不好的绝症,其实也挺简单,该吃吃该喝喝,开开心心过完剩下的日子也没啥;最可怕的是那些必须要动刀动枪的病,唉,那简直是生不如死。
我生过两个孩子,都是剖腹产。剖腹产很可怕,是从腹部横切一个大口子,然后把孩子拿出来。做手术过程中因为打了麻药,所以感觉不到疼,但是手术做完,麻药效力消退之后会很疼,要疼好几天。但其实,打麻药的过程也很疼。只是生孩子时,其它的疼都被宫缩疼掩盖了。
做别的手术就不一样了,打麻药的过程很疼,我觉得这个疼,可能还有一部分心理原因。因为我一进手术室就感觉到疼了,心里暗暗后悔选择做手术。恐惧的都是未知事物,因为不知道手术会有多疼。其实死亡不可怕,可怕的是未知。
进入手术室时,里面躺着一位刚刚做好手术的病人。我不知道她做的是什么手术,她好像睡着了,又好像没睡着。说她睡着了,是因为护士一直在喊她醒来;说她没睡着,是因为,她的呼吸沉重、杂乱,仿佛呼吸道里堵着很多东西。睡着的人,难道不是呼吸平稳沉静吗?但也许,病人并不一样。
我看着眼前的病人,心里越加恐惧、越加后悔。但已经进入手术室了,无路可退。我不记得,我躺上手术台的时候,那位病人推出去了没有。只记得恐惧占领了我的全部身心,我一直在做深呼吸,听着医生指令护士,一会时间,我的身体全被那些仪器监控了,手腕上扎着着针,在输液体,左手食指夹上了一个夹子,右小腿也不知包上了什么,胸口上贴了好几个带着线的小陀陀。紧接着,有一个小车车推到了我头的前方,我睁开眼睛能看到,我的正上方三十几公分的,是一圈方框架子。医生在给我的身上擦拭消毒药水,那冰凉的药水打到我身上时,我感觉到我的心脏更加紧缩了,可能是因为冷。然后需要开刀的周围全部用绿色的一种布围了起来,同时被围起来的还有我的脸,是从我正上方,那个方框上挂下来的布。我干脆闭上眼,再次深呼吸。
好安静,我听到,用剪刀打破小药瓶的声音;我听到,用针管抽进药水的声音;我听到,护士把针管递给大夫的声音。
大夫把手按在了我的身上,我知道要打麻药了,我使劲咬着牙。“啊,疼,”我忍不住,还是喊了出来。“马上就好,很快就不疼了。”是大夫的声音,可我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。也并非是疼的哭,只是莫名的心酸、难过。还好脸上盖着布,没人看到我哭。
麻了,要动刀的那个部位,彻底麻了,大夫拿手按压时,只觉得木木的,没有其它感觉。刀,我看不见大夫拿的什么刀,只听见嗞嗞嗞嗞嗞的声音。我身上的肉被割开了,能感觉到,大夫把那一块肉撩起来,手伸进身体里面,摸索着。好像摸到了什么东西,因为听到了,咔嚓咔嚓的剪刀声。大夫又重新按压了一遍,接着又听到了嗞嗞嗞嗞嗞的声音。这一次,我感觉,我的身上可能被割了个洞。好像大夫直接把那块肉给揭开了,然后直接在身体里面翻找着那个害我挨刀的东西。但是这一块隐藏的比较好,大夫是东抓一把找不到,西抓一把也找不到,然后把我的肉扯向左边、扯向右边。
莫名其妙的躺在手术台上的我,想到了挂在架子上被杀掉的猪。屠夫们拿着刀一条一条割掉了猪的身体,我从来都不敢看,只是有时候杀猪场设在大路旁,躲不过去,才会看到。但我从来都不吃肉,所有动物的肉都不吃,我觉得它们也会疼。因为这个我也常常被别人当作异类看待。
没做过手术的人,可能永远都体会不到那种痛苦,那种冰冷的器械在你温热的身体上作威作福的感觉;那种像挂在架子上的猪,把身体完全交给别人的绝望;那种不知道会不会留下后遗症的恐惧。
整个手术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哭,但不是因为疼。手术结束后,我暗下决心,这辈子再也不做手术了,哪怕因此而死掉!